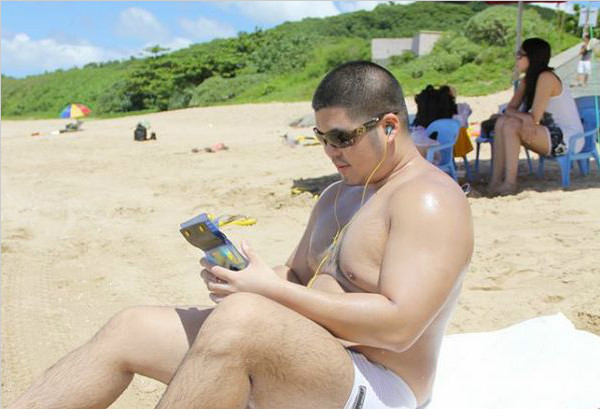雄性山林
左边一堆人围在坑上喝酒,个个挺斯文,一个王八壶依次传到每人手里,挺端庄地抿一口,又传给下一位,便慢条斯理地去翻人堆中间一大包乱七八糟的拆骨肉……右边一堆人也在喝酒,也围着一大包拆骨肉,也是一个王八壶,舞马扬炝,脖子上的筋蹦起老高:"喝!喝!你不喝不够意思,咱爷儿们喝!不喝酒长根鸟干什,喝……"
屋里一个铁油桶改的炉子发情般爆涨着热量。他左右瞅瞅,故意大声说:"喂,这样的天烧这么个大炉子纯粹多余……"
人们在喝酒吃肉,没人理他。
他真想哭。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根本没人明确地告诉了他什么,自己犯神经病,财迷心窍,从人家聊天中拼凑出这么条自作多情的消息……
他索性敞开怀松了裤带脱了鞋袜躺下,望着尿布样濡了块块水迹的顶棚,凄凄惨惨唱: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
不知唱过了几边,唱处眼泪头一歪就抹在臭烘烘的行李卷上……
他下定决心,大白天不能哭出声。
"小兄弟……"
有人捏住他搭在坑沿的光脚的大脚趾一提。
"干嘛?"
他一骨碌坐起来。昏暗中有个臃肿的人形,只有一张惨白的脸能看出是对他笑。
他的心跳成一团。
那人衡他呶呶嘴,打了个手势。
他身上立刻被注入一种魔力。他赶紧跳起去抓地下那双胶鞋,光脚有汗发涩,他看那人转身头朝前走了,他便拖拉着鞋去追。
出了屋门,满天星斗是个天高云淡的晴夜。
原来后边还有一间小屋。
屋里酒气熏天,他进屋咽了口唾沫。
"小兄弟,你也想去当‘棒槌客’?"
那人不看他,自顾往坑上爬。
昏暗中几双贼亮的 眼睛盯着他。
"恩。"他挺勇敢坚定地点头。
"苦哇!"那人已端坐在坑里被摞上,灯光下是一张不太让人讨厌,苍白疲倦的刀条脸,也就三十多岁。
"不怕!"石宝洁觉得自己是挺了下胸脯。
暗中有人说:"看样子是个下乡来的学生。"
"就你看得出来!"刀条脸汉子拧起眉毛冲暗处说,又指指坑边,对石宝洁说:"坐下!"
那汉子端过一杯酒:"喝!"
石宝洁接过,迟疑。
"好孩子都不喝酒,家长不让喝,老师不让喝。"那汉子叹口气,突然低声狠狠说:"想进山就得会喝酒,酒是进山佬的命!"
石宝洁端起咕咚干了,他知道自己还有二两的酒量。
那汉子冲他递过只鸡腿:"吃!你真想去?"
"是!"他点头。
"进了山,能发财还是运气。被人当流氓抓去,碰上狼豺虎豹,有个天灾病业,死在林子里可没人给你收尸。"
他盯着手里的鸡腿,没言声。
"跟你说话啦!"那汉子逼问。
"不怕!"
"真不怕?"
"不怕!"
"天塌下来自己顶着。"
"顶着。"
"说话算数!"
"算数!"
"把裤脱了!"那汉子突然正色下令。
他一惊,紧捂住裤带:"干嘛?"
暗中有又有人说:"人家是学生……"
"这屋里只有‘棒槌客’!"
那汉子声音低沉,却卷起阴冷的旋风。
坑里又有人说:"脱吧,这是咱进山的‘手续’,脱吧……"
他下意识起身后退了一步:"干嘛?"
"看你是不是男子汉!"
他听了,觉得刚喝的那一杯酒全涌到脸上。
满屋没有一丝声息。
那汉子叹口气,指着坑上一堆吃食挺悲哀地说:"好吧,拿点吃的,一天光喝白开水啃干饼子也该饿了,带够明天 路上吃的,你……回去吧……"
他慌了,问:"回哪儿?"
"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他愣愣站着。这一刻,他奋力使脸上那烧着的火退下,退回身上舔每一处又凝聚到心里,他一咬牙恨声说:"我脱!"
他褪下几曾裤。
没人吱声,只见几只火样跳跃的眼睛。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