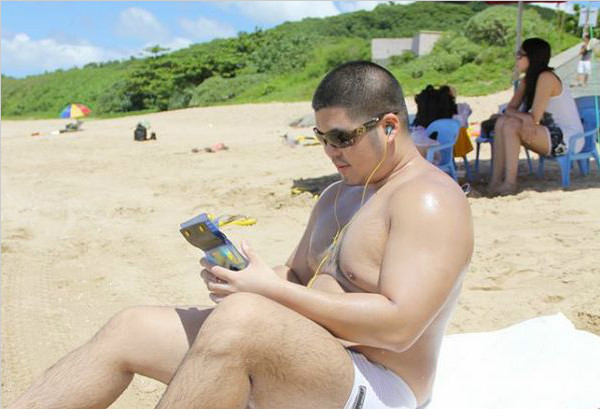痛爱
哀哀戚戚地,泪闪着黑夜的光,明了又暗,暗了又明,黑夜扑朔迷离。或许待到男人把酒都哭干了,把嗓子都哭没了,终于哭了个畅快。酒也渐渐醒了,语气慢慢肯定和悦起来。当男人自报姓名自报家门时,皓远却开始发怵了,他知道自己中了"计",男人的苦肉计——没料到在男人最脆弱的时候也是自己最慈悲的时候,竟拿"见面"去挽救男人的"离婚"。男人开始转泣为喜,八成是情绪转嫁给了皓远。"怎么会主动上钩呢?"皓远开始急躁不安起来,更多的是怀里揣了个"小兔子",忐忑着,既紧张又期望,要走出他同志的第一步,同时他又告慰自己,应该相信兔子是吃素不吃荤的。
男人喝醉了酒,说这一辈子从没与人这么聊过,从前也说过,不过这次让他相信了;酒后吐真言嘛。男人是真想见他的。他一看时间:哈!都过半夜12点了!又是四个多小时的聊天,天空划过了一道最亮的流星,说不定立马就要撞击地球了!
回宿舍时灯已灭了,皓远没来得及伸个懒腰就被老大恨铁不成钢的数落了一顿。竟是小蕾急了,向老大抱怨皓远一天以来没给她一条信息,这就叫追她么?远只是几次向老大说他挺欣赏她的主持才能的。老大就把这种好感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地延伸到要占有的地步了,就对女孩讲远已暗恋她多日。只是没想到女孩的反应这么大,莫非倒是女孩暗恋他多日了?——就当一阵风吧,春风吹过,万物复苏了,多情萌动、懵懂多事的春天也就过去了。皓远摇摇头,女孩?可能自己这一辈子都无福消受了。
"吱吱,吱吱,吱吱;……"整个地球都在颤抖,火焰不断地蔓延,那是在他们结束通话不足一小时后。应该不是流星撞击地球,撞也早撞得惨绝人寰了,是皓远的枕边在"燃烧",皓远拿起小灵通,有短信:
"夜,已深,虽然多数人不喜欢他的脸孔,但我觉得那特有的黑色中蕴涵着无限的光明。她虽然带走了归巢的河鸭,但我,小河依然流淌,哗哗的声音似在与我告别,又似你温和的声音,如同你在我耳边呼唤,同时勾起我多少年来的伤感的回忆!晚风却将痛苦的回忆化为春耕后泥土的芳香,夹杂着春雪融化后的湿润,就如同你泛泛而红润的脸颊。我思潮畅涌,回眸着刚才的冲动,回想着向你倾诉的傻痴的话语。猜想着你讥笑我无知和痴情的样子。忽地,身后车子里传出忧伤的乐曲——游鸿明的《白色恋人》,唰地拉开了我对你思念的珠帘,远处的街灯明了,让我从思绪中解脱出来,促使我又拿起了电话。我似又听到了你的声音,激起我无限的兴奋。我笑,笑的很快乐,笑的很幸福。但也充满了无法说明的苦涩和失落,我多么希望永远的笑啊!可是我却不知道天明后会不会笑了!夜风早已送走了阳光留下的温暖,吹来山上花木盛开的清香……我似乎看到无数夜空下的爱情,我真想那里有我的一分子,我真想永远地对爱和情尽情饱尝!真的,永远!永远!永远-…"
皓远泛着夜光的近视眼也不知睁了多久。天一明,他似乎就要投入某人的怀抱中去了。
皓远早早地起了床,上大学以来第一次刮了胡子,因为视频时男人说整张脸都挺漂亮的,就胡子太冲,像唱京剧的美旦偏偏戴了个络腮胡。远端详着镜子中的自己,整一个小白脸,再不那么忧郁而苍凉了,敷了次面膜,痘痘的痕迹在辉光中消失殆荆再用啫喱水将耷拉着的头发向天空拉了又拉,似要做那接收天籁信号的天线,根根发丝都精神抖擞,翘首以待。
男人叫天涵,明明天气越来越热,他却叫"天寒",念着这名字竟象吃冰淇淋一样,有点料峭.天涵还在路上就叫远起床了,不到7点,故意要叫他早起整改一翻。平时周末他肯定是要三四小时后才起床的。远在穿衣镜前挤眉弄眼,搔首弄姿地舞了几十圈后男人才终于到学校了。接到电话的远有些发抖,机能似乎失调起来。他跺了跺脚,搓了搓手,告诉自己是冷所致,又对着镜子弄了几下头型,旋了几圈,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楼去。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