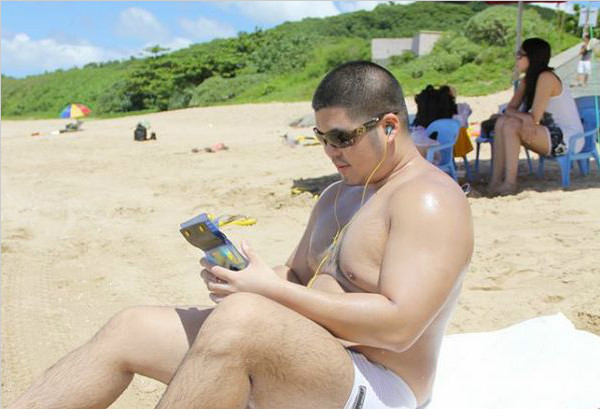我和表叔的故事
"好啊你,我看你是欠叼了啊。"说着就追了上去,街上的人都纷纷避开我们扬起的尘土。如果能一直这样,和爱着的人一起爱着,和在意的人一起生活着,那就好了。晚上因为绍军要去陪他亲爱的师姐自习,所以搜集灾区图片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宿舍的人回来洗澡然后又出去了,七点半剩下我自己一个在宿舍对着电脑。好,是时候开始面对了。打开浏览器,Google,"汶川"词条,Google图片。一张一张地挑,从灾区现况到灾民们的生活情况都一一下载。看着看着,我只觉炎炎夏夜的宿舍刺骨地冷,额头冒着冷汗。蝼蚁。我只是只还在继续潜行的蝼蚁,而遥远处有同胞失去了生命,而我还依然需要在路上继续。他们也有自己爱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只是突然地失去了全部。万一,有天轮到我了呢?我们是暗黑宇宙中一点星尘,时间和空间概念里不值一文,千百万亿年和无穷尽的维度里,我们不过沧海一粟。如果……死的是我呢?表叔也会这么悲痛吧?可是如果……先走的人是表叔呢?这些各异的想法如同妖魔封在葫芦中一样,撞击着葫芦内壁发出阵阵声响,我感觉它们快要破壶而出,獠牙发出的腥臭漫遍整个空间。我右手点击着鼠标一张又一张图片地看着,脸如同被泼了水一样都是眼泪。左手握着手机越握越紧。翻开电话本,下翻页,"鹿",拨打。没接通就被我掐息。表叔,你知道吗?那时我多想我能够理智地面对生死有命这四个字,我多希望在我软弱的时候想到你能够做到永远不找你听我哽咽。你是我的男人,可是我也是你的男人。你说过你要保护我,可是我也想把我的臂弯伸给你。可惜我永遠不會說,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还好还有 Side-A还好还有-Side A人与人,有时很像排着队向着未知方向进发的蝼蚁,掐掉几只或者冲走一片,剩下的在短暂慌乱后又会继续向前爬行。低等吧,或许它们也会有担惊受怕,仅是无能为力而已。
2008年对于我来说,除了那场遥远的奥运盛事,便是和表叔的热恋以及汶川的悲剧。
沈晏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习惯趋利避害的人一样,总下意识地逃避面对悲伤的事情。悲剧发生的那段时间,刚陷入热恋的我当然也为之悲戚。
还记得5月中旬,每次课间都会有同学在投影上看新闻,关注千里之外的灾民的状况。我都避之不看,我害怕,害怕那惨况除了带给我无穷无尽的悲伤之外,还会令我陷入更为无边际的有关生死无常的无力感。
绍军一直想以部门名义办个募捐活动,但碍于部门职能关系一直未能获批。而学院终于有了募捐活动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中了,虽然是红会主办,但大家还是抱着身为学生干部理应一起工作,以及为灾区贡献努力的心全力协助。
接到绍军的电话时,我正坐在表叔家的饭桌上边抽烟边看书,表叔在整理衬衣和领带准备去工作。
"绍军,怎么啦?"
表叔听到我接了绍军的电话,有点探听意味地走了过来。
"你去哪啦?你宿舍的人说你好几天没住宿舍了。回家了也不说声。"
我站了起来,揽着表叔的腰,捏了捏示意他放心,我还没斗胆到又惹他。我知道表叔会吃绍军的醋。表叔摸着我没穿衣服的小腹,斜眼看着我,用眼神跟我说"我就要听你讲话,怎么了"
"谁跟你说我回家啦?我在亲戚这,宿舍太热了。"
"哦。红会要办赈灾募捐,我们部门要负责搜集资料和展板赞助。想叫上你和我一起去而已。"
我看了看表叔,他没说话,大概是没听清绍军说什么。
"好吧。我也只是在看书而已,我下午回去再找你。反正第一科考试也很快开始了。"
"嗯,回来就找我吧。"
盖了电话,表叔满脸问号地看着我。
我凑上去亲了下他,"学院要弄赈灾募捐,我要回去帮忙,而且第一科考试没几天就要开始了。我回去啦?……鹿?"
表叔听到我第一次在非短信交流情况下这样叫他,扑哧地笑了。
"回去吧。上次我已经以我们名义捐了1500块了,还不够。这下人力也出了,应该的。"
"我就知道我条仔是相信我的。"我笑着对表叔撇了撇嘴。
表叔反手伸进我没绑紧的沙滩裤裤头,捏着我的那里,"嗯。不过如果给我知道你们又拉拉扯扯的,小心我打死你。"说完还用了用力。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