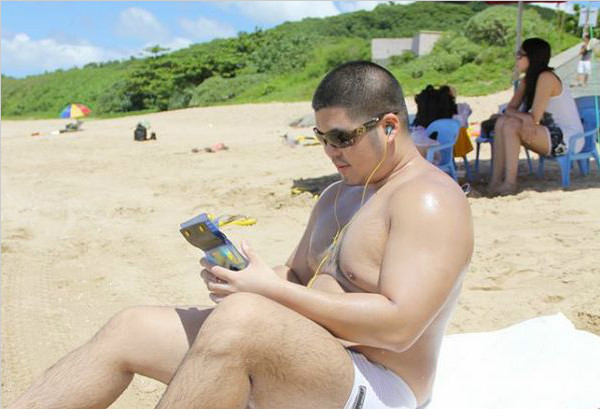长海叔
"知道,苏烟有抽过,很淡的,厂子里工会杨主席常叫我帮他洗车,有时会给个整包,很好上口。哎,对了,叔可不可以拿苏烟去小店换蹩脚一点的烟抽?一包可以换三四包呐?"说完,神情有点专注地看着我,就像一个刚交了试卷的小学生,正等待老师的评判。
我哑然一笑,觉得长海叔真有那么一点点可爱,就顺水推舟地说:"好吧,但是只能换一条,还有一条得留着自己抽,我要检查的哦!"
"好嘞,保证只换一条!"长海叔很爽快地答应我……
长海叔觉察到了我手部的动作,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故作严肃的说:"还不松手,叫你桂芬姐看见了多丢人。起床啰,听话。"
"看见就看见,有啥关系麽!"嘴上虽然说着,手还是放了下来。长海叔站起身,帮我从椅子上拿来衣服。我看见长海叔站直的时候,裆部被顶得老高,也真有点怕桂芬姐突然闯入,看见这尴尬的一幕。
心情已经无比舒坦,不由吹起了口哨。
只是幸福甜蜜的时光,总是显得那么短暂。
院子里静悄悄。火红的石榴果在秋风中颤动,宣告自己的成熟。枯黄的枣树叶一片片随风飘零,纷纷扬扬洒向地面。老迈的家猫蜷缩在外婆的棉鞋中,迷糊地打着盹,没有正面看我一眼,只有厨房后面,传来洗衣机断断续续的嗡嗡声。
看来桂芬姐上集镇买菜去了,我隐隐有点后悔起床太早,或许我应该在床上多呆一些时间,多享受一点刚才醉人的温存。趁我洗漱的当口,长海叔拿出几只荷叶包着的豆沙馅糯米团子,给外婆房里送去。这些糯米团子肯定是长海叔表姐送给他的,他拿来孝敬外婆,真难为他心肠这么好。我也要待长海叔这么好,我暗暗下了决心。
我听到长海叔在跟我外婆讲,中午会留我在他家吃饭,叫桂芬姐不要等我了。外婆照例说了很多客气的话。喝完稀饭后,我们一老一少向江滩走去。
今天天气真好,气温回升很快,好久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呼吸这么清爽的空气,让我想起了"碧空万里"这个词。拐上江堤后,极目远眺,长江入海口的江水和天际线分辨得清晰可见。水面上不断地有各种水鸟起飞和俯冲,享受着迁徙前的最后盛宴。
解开拴住小船的缆绳,我帮着长海叔将小船推进潮水。长海叔在船篷里换衣服,在我的坚持下,长海叔在皮兜下保留了松松垮垮的平脚裤。我再一次仔细观赏到长海叔壮实的身体,禁不住佩服地问:"叔,你都四十几了,身胚怎么还这么好啊?"
"哦,都是扛纱包练出来的呗!"
"什么扛纱包啊?"我觉得有点奇怪。
"在棉纺厂呀!把二十个纱锭打成一包,缝好头,再扛到库房,堆整齐,码好。一个纱包要五十多斤哩!"
"那你不是在棉纺厂做保安吗?怎么又要去扛纱包呢?"
"赚点外快呀!做保安上班清闲,下班后又没地方可去,闲着也是没事,一天打两百个包,一毛钱一个,可以赚二十来块钱!"
"那要扛多久啊,两百个纱包,都累死人了!"我发出由衷的惊叹。
"哪用得了多少时间?做顺了很快的,不到两个小时就歇手。"长海叔转过头来,露出轻松的神态,似乎刚扛完了二百个纱包,一点都没有气喘。
"怪不得叔的身体这么壮,每天都是在锻炼,我眼红死了!"我现在随便什么花言巧语都不用打个草稿,就能脱口而出。
"叔这身体算个啥,比我壮实的人多的是,搬家公司的老刘有我两个这么大!"长海叔一边说,一边捏紧拳头,屈起右臂,露了露鼓起的肱二头肌。
"搬家公司?"
"宝啊,叔做保安队长,每个星期天都有休息的,叔闲着没事,就去搬家公司打打零工,城里人搬家都是挑星期天,所以这天的工价最高,一天要八十块钱哩!对了,搬家公司走过去也近,就在我那个厂子边上。"
"叔,你还去帮别人搬家?"我几乎不能相信,人家都以为长海叔在城里做个清闲的内保,哪知道他什么都干,每天下班后扛沙包,休息天去搬家公司卖体力,对了,还要给工会杨主席洗车。
"那你做保安一个月有多少工资啊?"
"很少的,千把块钱吧,厂子里效益不好,常常拖几个月发不下来。不过扛包费倒是每天都算清的。这种活本地人不愿干,都是些外地人在扛。我有的是力气,歇一晚就长出来了,不用也是浪费了。"
"看你这么节省,又要打外快,一定攒了不少钱吧?"我吐出舌头,表情夸张地试探着长海叔。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