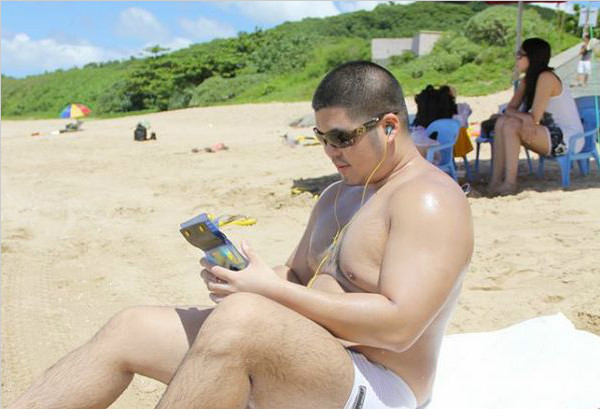熊父相守
"你肖叔……"爸爸说,我敢发誓,这并不是他的声音,绝对不是我平常所认识的那个爸爸的声音,而是从另一个是里发出来,是的,是从肖叔那个世界里发出来的声音,那声音不属于我和他所组成的空间,而是他和肖叔的。
"他最喜欢下雪了。"他说。
哦,肖叔
那场雪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渐渐的停了下来。
我虽然躺在床上,可一整夜,我都能感觉到外面雪片飘落着时候絮絮的声音。
我也不记得我到底有没有睡着,我用被子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盖的严严实实的,有一段时间我坚信我没有睡觉,可再过了一会儿我就不确定了。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为什么我会产生一种疏离感,我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那场雪的关系,这个城市每年的冬天都没有下雪,可就树这次下的最大。
我感觉到躺在被窝里身体也像那些从天而降的雪花一样飘舞在空中,不同的是它们最终会飘到地上,有的落在大街上,树枝上,墙角里,或者行人的头发里,总之它们总会慢慢的消失,变成气体再次成为空气的一部分,然后再次循环形成雪花。我躺在被卧漆黑不透风的空间里,想象着他们这样的命运,同时我也想到了我自己。
它们永远的循环永远不会消失,而我,我呢,将来会长大,18岁,20岁,30岁,50岁,直到我死去,而我死去了就死去了,我的躯体开始腐烂,最后只剩下一堆干净的骷髅,可那些还活着的人连骷髅都不想留下来,他们会把你的还没有开始腐烂的尸体推进火葬厂那个巨大的火炉子里,把你烧成粉末状的灰烬,然后巧妙的把这些装进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这些粉末,你相信吗?这些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灵魂会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人。
那个晚上我想到了死亡,我感觉自己有点害怕,但我不是惧怕死亡,而是死了之后会怎么样?是漫长无尽的黑夜吗?你的灵魂就像那些雪花一样漂浮在这个黑夜里,永无尽头?那还会是怎么样呢?
这才是让我感到害怕的,因为我当时有个倔强的想法就是无论怎样,我现在还活着。
我想,我确信我醒了过来,因为我模糊的记得我刚才做了一场梦,只是刚醒过来我还没能完全从梦的意识中摆脱出来。我之所有醒过来,是因为我隐约听到了男人的哭声。
而这声音就在我睁开眼睛的一刻就知道是爸爸的。被子还蒙着我的身体和我的头。我的眼睛能感受到的只有黑暗。
"好象死了。"我突然默念出一句这样的话。
然后把被子拉了下来,我的房间虽然没有开灯,可从门的缝隙里映进来的客厅里的荧光灯,还是冲淡了房间里的黑暗。我确信自己不是在梦里,而且还活着。
我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爸爸的哭声很轻微,但我仍能听的那么清晰,周围静的出奇,好象整个地球都没人发出什么声音。我仍然坐着,就那么坐着,我想着出去,告诉他最好不要哭,不要让自己伤心,可我就是坐着动不了,好象自己一不相信被变成了石头像没有了任何知觉。
我听见爸爸吸了几下鼻子,结束了自己的哭泣,然后是一连串软闷的声音,他的脚踩着地毯在走路,可那声音仿佛被赋予了真正的生命,那么活灵活现,那么真实,我从没感觉到如此真实的声音,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听见过。他是向我的门口走了过来。
我有点焦灼,我在决定是继续坐着等他打开门还是躺下来装成睡着的样子。但我仍做不出真正有效的决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了决定。但我的身体还坐着,爸爸的身影在狭窄的门缝里闪了以下,我能看见穿在他身上的白色的棉制睡衣,胖胖的身躯在那个细长的缝隙里微微的晃动着,他没有决定立刻推开我的门。
但我的身体还坐着,爸爸的身影在狭窄的门缝里闪了以下,我能看见穿在他身上的白色的棉制睡衣,胖胖的身躯在那个细长的缝隙里微微的晃动着,他没有决定立刻推开我的门。
门还是被他推开了,没发出一点声音,周围更是静的出奇,仿佛这个世界失去了声音,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
他的脸显露在我的房间里,可他身后的那片银白色的荧光灯把他的头发和肩膀靠后的一部分都映耀成白色,仿佛镀上了一层银边。可他的脸埋在我这边昏暗的空气里,一片模糊,我想我在他眼里也是一片模糊,他甚至都不会怀疑我为什么这样直愣愣的坐着看着他。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