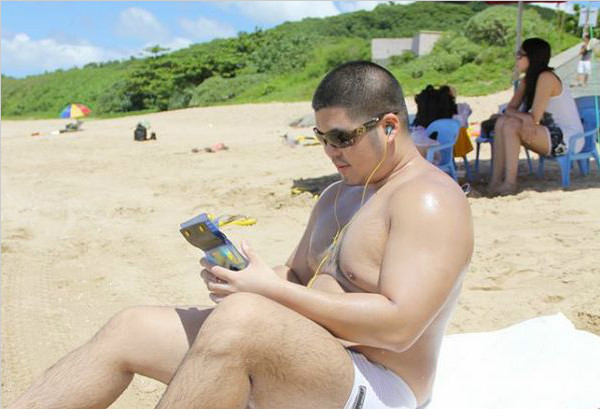早雾晴 晚雾阴
"是啊,可惜君儒是个大老爷们,要不我就上了,哈哈!"他笑着把腿翘上了我的身上,我趁机摸着他的肚子,他赶紧拿手打了我一下。
"摸什么摸?!只许我摸你,不许你摸我!"
"哈哈,霸道!"我埋怨了一声,扭身把脸冲向了罐哥,蛋哥还是抱着我不放,他笑着说:"不是霸占,等我的被窝被你暖热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可以去你罐哥被窝了,哈哈!"
罐哥也不答话,只是偷偷地把手伸进来了,摸在我的腿上,但蛋哥突然喊了一声:"君儒!把被子压好,都跑风了!"
罐哥赶紧把手抽回去,无奈地笑了笑。
我被蛋哥搂着睡不着,他却打着呼噜睡得很香,但我一翻身,他就会在我身上打一下,并嘟哝一句:别乱动!
清清终于和父母和好了。她这个人一会儿一变脸,晚上说的那么慷慨悲壮,第二天她那傻小子对象一说点软话,她就把晚上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都抛到了九宵云外,跟着傻小子高高兴兴地走了,好象根本没什么事似的。不过后来听她说,她妈一晚上没找见她,都疯了,所以答应了不再追加彩礼,这才让傻小子找到她回了家。不管怎样,清清的夜不归宿还是有效果的,起码整治了一下她的顽固老妈,使她以后在婆家的地位做了个很坚实的基础,那傻小子以后估计更是对她百依百顺不敢有丝毫怠慢了。
老程回去都六七天了,也不见回来,说好了在家住两三天就回来去北京的,怎么还不回来?我很担心,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这几天因为他我都快成神经病了,满脑子都是他蹒跚的影子,做梦也都是他被疼痛折磨的咧嘴的脸。
下定决心要去他老家把他接回来,毕竟去北京看病才是主要。本来蛋哥和罐哥说一起开车去接他的,但现在是旺季,两家都离不开人,所以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随行,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就走了。
汽车在盘山的马路上颠簸了近六七个小时才到了他们村所在的乡,这里离他们的村还有十五里,而且都是山路,汽车根本过不去,我必须步行走了。
打听好了他们村的方向,我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上走去。
说是走,其实就是爬。因为我已经感到了行走的困难,和在平原那样潇洒地走是两种感觉。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早点见到他,哪怕再陡的山坡我都愿意登上去。
终于在天黑之前我到了他们的那个叫"白土"的村。以前听他说过白土村的来历,传说是观世音在一个灾害年洒下了甘露,救了这一方百姓,被甘露浇灌过的土地成了白色,所以以后这个地方就叫白土了。他还说在他家后面的山坡上建了一座观音庙,香火非常旺盛。
村里也是忽上忽下错落有致的房屋,我对这些很好奇。没见过这样的房子,这家在那家的房顶上,我有点兴奋,但疲惫的精神却不能使我表现出来,现在的我只想马上见到他。
"柱子,你家来亲戚了!"一个老人带我进了一个院落,房子的后面隐隐约约看到黑屏障似的山坡。柱子估计就是老程的侄子的名字。
"来了。"答应的是个女声,随着话音落下,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从屋里出来了。
"我是程叔的朋友。"我把老程的称呼改了。
"哦,进来吧。"她的眼里透出兴奋,"快进来吧。"我向领路的老人道了声谢,跟着这个女人进了屋子。我期待着进门会看到老程,但使我失望的是除了破旧的家具和一堆脏衣服外,就只有她们娘四个了。
"程叔呢?"我问她。
"哦,还没回来呢。你坐啊。"她把放在椅子上的脏衣服扔到床上,给我腾出地方给我坐。
"去哪了?"
"柱子带他去临村扎针了,现在应该回来了,你先坐着,我给你盛饭。"
"不了,我等等他们吧。"
"要不你先喝点水。"她拿来一个暖瓶,然后对其中一个最大的孩子说:"去村口接接你爹和你二爷,就说来亲戚了啊。
孩子跑出去了,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老程最近的情况:"嫂子,我可以这样喊你吗?"
"可以,我是他侄媳妇,你就喊我嫂子吧。"
"哦,程叔现在的情况怎样?"
"唉,刚回来那一天把我们都吓坏了,疼得在床上打滚,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柱子把他背到临村,人家给他扎了一针就不疼了。"
"哦。"
"但是他却说不管用,天天喊疼,奶奶也受不了他那样的喊叫就让他搬到我们家了。我一个侄媳妇伺候起来也不方便,柱子在那伺候他。"
"哦。"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