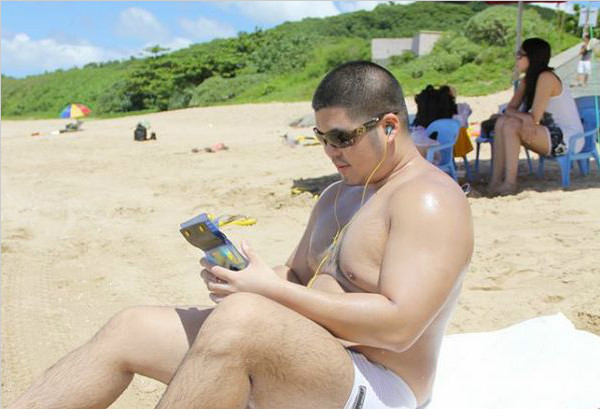中年男人和毕业生合租
到了老家,母亲已经基本不能说话,但是还认识我。一周之后,母亲陷入了昏迷。当母亲的手和脚渐渐变凉的时候,家里人开始为她穿衣。这时候,哥哥发现为母亲准备的褥子里子带有红色,就一把扯下来,让嫂子赶快换上另一方棉布,要求用一根线,不能断。嫂子当时已经方寸大乱,刚缝了几针,长长的线已经纠结。换上姐姐,姐姐的手也已经颤抖得不知所措。我说,我来。嫂子和姐姐在一旁辅助,我咽下母亲即逝的沉痛,稳定心神,拿起针线,一气呵成。看着母亲躺在木板上,已经气若游丝,我抚摸母亲冰凉的脚踝,泪眼滂沱。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口众多,父亲常年在田地里劳作,母亲伺候一大家的人,有时候根本就照顾不过来。课余时间我下地帮助父亲干活,衣服、裤子坏了的时候,自己就拿起针线,学着母亲的样子缝补,这项技能在外地上学的时候也得到了施展。
期间小冬来过几次电话,他让我替他给母亲磕头。每一次和他通话的时间都很长,家里人看到我在院子里打电话,可能都觉得纳闷儿,但是没有人问我。
夜已经很深了,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望着天上的星星,我在寻找天堂,在向天堂的方向张望…
母亲走后,我才向家里的亲戚们说起我已经离婚的事情。大家了解我的前妻,除了关切地问起我的生活,对于我的离异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回到家里,小云让小冬请我吃饭。看着我满脸的憔悴,小冬默不作声。喝着酒,想起母亲一生的辛劳,我的眼泪已经淌了一脸。
大约三个月,这是我恢复的时间,从悲伤中恢复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忽然想疏远一切人,我删除了QQ里的好友,下班之后我就把手机一关。只有小冬有时候就过来看看,有时候领着五一,有时候路过。我很少说话,有时候就一脸肃穆地捧着本书看,有时候闭目养神。小冬也很少说话,帮我整理整理房间,或者顺手给我做点吃的。如果五一在场,我还会流露出笑脸哄着他玩一会儿。
悲伤过后,我发现自己的心已经被清洗过一样,什么也没有,清澈而透明。我不想再探寻自己的内心,一个人越往心里走,就会越累,最后走进一个死胡同才发现,想要转身已经没有气力。
简单地生活多好。上班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各种各样性格的同事笑颜相对,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以自己的温情缓解同事由于工作紧张带来的焦躁;下班之后全身心放松,偶尔冒出关于工作的思绪马上戛然而止,我的业余与工作无关。每天都安排固定的时间去打球,不能说是用打球来排遣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是我需要健康的体魄来面对以后的生活。
在我的内心里,小冬是可以在内心里偎依的朋友,目前的小冬已经由青涩蜕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尽管不能朝夕面对,但是心里总会有一种淡淡的牵挂,这种牵挂徘徊在我内心敞开的门扉前后,在这种情绪之风的吹动之下,心扉的铁质门环因此而经常被甜蜜地叩响,我也相信这样的感觉如同小东家的窗口随风摇曳的风铃,经常在夏季的黄昏叮当,温暖小冬不经意间注视的目光。有时候也会想起浅尝辄止这个词,具体的明确意思已经忘记,虽然百度的功能很强。
对于未来的规划,显然还不能有一个定论,生活不会按照你的规划而改变既定的轨迹。但是很显然,想尝试经历一场轰烈的情感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
有时候我也想疏远小冬,但是我还真没有疏远他的理由。作为一个深交多年的好朋友,毫无理由的疏远对人的伤害太深。小冬是我唯一的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失去了这唯一的朋友,我的生活会不会更好。
尤其是在夏天,江边是人们消暑散步的好去处。小冬喜欢游泳,我却是一个旱鸭子。我和五一在江边的潜水里肚皮贴地爬泳,小冬一次又一次地在很深的地方来回畅游。
小云出差了,小冬把五一送到了姥姥家,单独邀请我下班的时候去江边野餐。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