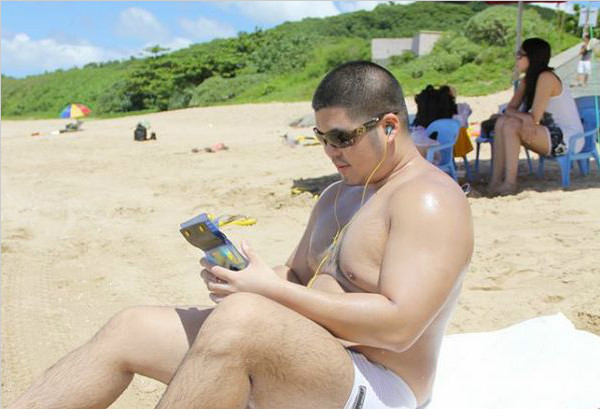两个男人的流年错爱
手术结束了,医生走出来只简单的和他交谈了两句,雷家现在只有雷一扬一个人,公司里的那些股东不过是生意场的合作伙伴,对这个执事者的生死并不在意。
两个人都混混沌沌的活了几十年,到头来好像可以互相依靠一下的,还是只有对方。
可是接下去,许默怕自己连他都要失去了。
擦伤,骨折,这些几乎医生提都不提,只是告诉他,雷一扬的肋骨被撞断后**了肺部,造成大出血,颅内出血也相当严重。
不过许默完全听不懂,还是愣愣的盯着医生看。
其实他想听到的,只是这个男人没有事的保证而已。
虽然,他打碎了花瓶,藏起了那块锋利的碎片;虽然,他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那块碎片在他脖子上划过的样子,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男人会是这样死在他面前。
"医生——"他好不容易听到自己发出声音,也是颤抖着简直可笑,"他,没事吗?他没事对吧?"
医生看着他,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个一脸懵懂的男人根本没有听他到底在说什么,这样的伤,还可能没事?
看惯了生死的医生对于一个人能否生存下去总是没什么感觉的,冷冷的告诉他:"如果今天晚上,他可以挨过去,大概还有救。"
听到这个结论的许默简直忍不住就要笑起来了。
到头来,是要他等这个男人幸运的活过来。
十几年的时间,纠缠不清的恩怨过去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当初那个单纯的关系上——他要等这个男人。
他曾经安静的等了他七年。
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任何承诺的等,终究没有等回到自己希望的。
然后受伤,然后互相仇视,到了最后,他居然还是得等他?
他们之间,还有多少的时间这样等待下去?
慢慢的到了午夜,应该安静的时间,许默被一阵喧闹吵醒了。
睁开眼睛看,眼前那个男人深深的陷进了柔软的病床里。因为是雷一扬,他的病房是全市最豪华的,器材也是最先进的,甚至有护士殷勤的在窗台上放上了鲜花。
他的脸颊很深的陷了下去,原本俊朗的五官显得更加棱角分明了。和七年前分开的时候不同,现在更加成熟了,可是即使不笑,眼角也看得到一些淡淡的皱纹。
许默自己也有皱纹了,不去想的时候不会觉得,可是看到他的时候真的知道,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可是,却没有什么是在手上的。
他伸出手去,轻轻地触碰这个人的脸,有点出人意料的粗糙感,下巴处也有些扎手,大概是有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触摸的时候感到骨骼分明,非常的瘦。
他,似乎也过得并不好。
直到有轻微的铃声响起来,许默才惊觉自己把手放在他脖子上很长时间了,力气也有点重,急忙缩回手来。
在病房安静的空间里,铃声即使不大也显得有些刺耳,许默站起来找了找,发现是挂在一边衣架上的雷一扬的西装里传来的铃声。
他走过去拿出来看,是国外的号码,正在犹豫,铃声停了下来,大概是太久没接听,自动挂断了。
微微松了口气,正准备放回去,铃声却又在手里响了起来。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在对方开口之前,走到了阳台上。
谁知外面喧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几乎要转身在走回病房里,却在听到对方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呆在原地,连动也不能动了。
"雷一扬,是我。丁静云——"
只是当时已惘然 流年
他的大脑一瞬间空洞了。
外面那么吵闹的声音,也比不过这句简单的话给他的冲击来得大。
等到大脑开始思考的时候,对方似乎已经说了好几句话了,而他一句都没有回。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抖着,控制不住力气,手机机身发出吱嘎的声音,快要被他捏碎了。
他磕着牙才勉强的说:"静云,是我。"
对方也一下愣了,立刻声音高了好几度:"默哥?默哥,是你吗?!"
"是。是我。"他还是抖得厉害,"你,你在哪里?你们怎么样了?"
丁静云也很激动的,听得出声音一直在发抖,支支吾吾了好久才总算定下神来,清楚的说了一句话:"默哥,我们现在在瑞士。我,嘉齐,还有天浩,我们在瑞士的疗养院里,是雷一扬给我们安排的。"
许默的嘴闭得很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