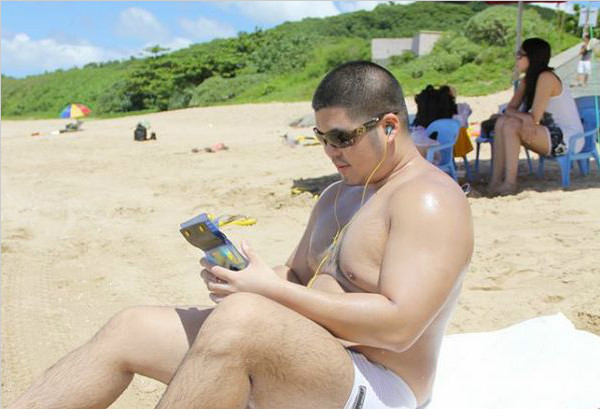雄性山林
"你长着嘴,我长着耳朵呢。"
"嘿,其实,我想不透,你是个‘知青’,大城市下来的学生,咋也想进山呢?"
"大山林不是人进的吗?"
"其实,我挺佩服你,冲你闯进大山林当了‘棒槌客’这份胆气,看你是个男子汉!"
"男子汉?不进山就不是男子汉了!"
"不是,我是说,你……你不像顺子。"
"顺子怎么啦?顺子哪点没比你做得少,顺子照样和你一样钻山趟岭,……"
六头诧异地看着他。
他用从未有过的坚定也看着六头。
突然,六头从被窝下伸过一只手死死攥紧了他的手。六头的手又热又粘,他想挣开,六头却不放松,他越挣,六头攥得越紧。他听见六头胸腔里呼通呼通在挣扎撕掳着,他听见这声音心便先软了。他轻唤六头,用一种告饶乞怜的眼色看六头,而六头却扭过头去不看他,只在扭头的瞬间眼里闪过一层惊慌和懦弱……
老宋又在唱。
他任凭六头那只又热又粘的手攥紧自己。
"石头,你进了山,你们同学不找你么?"
六头轻轻问。
"我们……知青点,早散了。"
"其实,其实,有福之人不会落无福之地,今后,你们,还会出人头地,不比我,脸朝黄土背朝天,这辈子就和土疙瘩过日子了,……"
六头用从未有过的亲近安慰他,话语里却难藏自己的悲哀。
六头仰面躺着,不看他,只是那只手在宝洁身上滚过一阵阵发粘的烫热。
又有一声炸雷爆裂。
宝洁却不推开六头的那只手。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六头挺可怜的,觉得六头也和顺子和他一样,甚至和老宋一样,在少年的雄性身体里,涌动着对同性身体的那种莫名的强而有力的欲望。
他有想起了顺子。
他曾追问顺子这是怎么回事,顺子却根本说不清。他也追问在老宋的窝棚相遇的那晚,顺子为什么非要证明老宋身体的残缺,却又和宝洁做出老宋不能做的事。顺子告诉他,顺子早就想接近他,顺子和老宋的接触好象有种不很情愿,而和宝洁,才感到称心的欢悦。
而现在,六头对他的一反常态,又是他哪根神经的驱使呢?
六头的那只手在顺着他的胸脯往下移动。
"六头……"他暗中捉住了这只手。
六头纹丝不动,只盯着棚顶被惊雷震得颤抖不止的一根枯树枝……六头的手就停在他的胸脯上,停在他那颗一炸一炸要并碎的心上面。这可心好久没这么跳过了,六头似乎怕它回炸裂,暗中使着劲往下按……
又是惊天动地一个炸雷。
"起吧!起吧!"
老宋突然撕心裂肺地在叫。
钻出窝棚,扑面的硫磺味。
那个堆着干蘑菇干木耳干药材的棚子里窜出了腾腾的浓烟,那浓烟是从老宋身子底下冒出来的,老宋整个身子趴在那堆东西上。
"快,把这些搬了,快,六头,去拿东西,拿棉被闷……"老宋嘶喊着。
六头应声去了。人们七手八脚搬那些东西,老宋催促:"快,快!让烟一窜就全完了!"
半晌,没见六头出来,老宋喊:"六头,你得暴病了咋的……"
"拿哪个呀?"六头问。
"拿啥不行?难道扒了你的皮不成!"
……
东西搬开了,老宋被搭下了,前胸和肚子满是晶亮的大水泡。
他咬牙说:"石头,吧我的酒壶拿来。"
石宝洁带了哭声:"老宋,你得下山,你得去医院呀!"
"石头,医院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吗?"老宋躺着咕咚喝了一口酒,没起火是万幸。石头,要是起了火,咱们都是死罪。"
他让人们去挖几颗‘黄瓜香’(地榆)来,他说捣了敷上,有三几天就好了。
他苦笑说:"石头,学着吧,靠山吃山,混山的偶凭着山神爷的赏赐度命……"
人们挖来了‘黄瓜香’,却见老宋原本苍白的刀条脸黑漆漆的,只以为他是疼。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