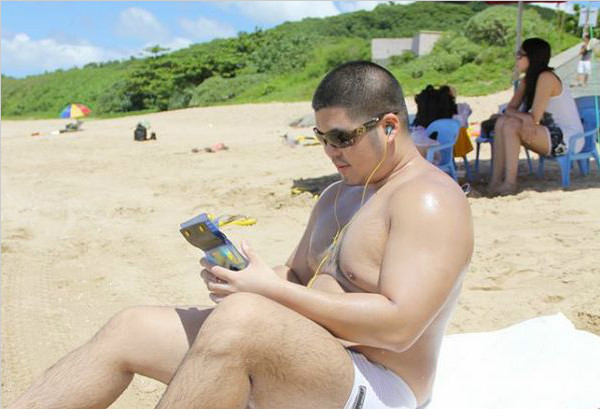转角遇见熊爹
「牙牙,开回去好吗?我怕真的是我昵桑倒了。」阿翼眼神中透着担忧。牙牙开着车,不满的回着:「屁啦,要去看,你下车,我才懒得开回去看是不是那糟老头,这种家伙不值得你留恋啦!」回去看的念头又压抑了下来,就想说是别人倒下吧!可别真是昵桑才是,阿翼心中如此想着。...
无心看小说,更无心读日语,想着与熊爹尔后的关系变化。阿翼躺在床上,双眼直盯着天花板陷入沈思。
「感情果真得如此委曲求全?如果让自己过的不快乐,要这样的感情做什么?如果熊爹心不在我身上,早早结束掉这段感情或许对两人都好不是?」「上次的谈话大概就知道熊爹和其它汤友有在互动,只是,没想到,那种互动竟是更甚于自己一层的关系互动。我也希望自己和昵桑的关系能融入生活,融入休闲啊,我试着借着调动来缩短我们的距离,试着藉由购屋来增进两人互动的机会,但,这一切的善意改变换得的又是什么?」
泪水一直从眼角淌下,顺着耳际低落在枕头的头套上,那是熊爹送阿翼的一对枕头套,上面绣了两只白熊,脸颊交触着亲昵。如今,泪水似要冲离这亲昵渐往疏远。
「远距离的感情,难道注定就得伴着等待,伴着思念,伴着让人胡思乱想的念头?」「年龄的落差,难道就注定不能融入对方的生活,和对方的生活打成一片?如果熊爹没有进一步的作为,我想,我和他的感情到最后仍会无疾而终,仍会石沈大海的。」莫非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莫非自己在圈内的老练换得的是如此不堪的结局?
侧了身,阿翼拿起了桌上的双人照,是阿翼和熊爹在摩天轮请人合拍的照片,两人彼此搭着腰际,一副恩爱似父子合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目前收藏唯一的一张,也是阿翼在睡前最容易伴梦入睡的一帖良方。
阿翼从照片架后取出了照片,深情的望着照片里的熊爹,对着熊爹深深的献了一个吻。瞬地,将照片撕成两半、四半、八半、十六半,猛力地往上一抛。碎身的照片如雪片般的纷飞,在卧房的一隅划着不规则却又让人心悸的痛。
「和熊爹一起来泡汤的那位胖胖中年,气势好咄咄逼人。在他眼中,或许,我是第三者吧!在熊爹眼中呢?我是不是也只是尝鲜的菜肴而已?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界定,还是成全他们好了。以前也教过学生『君子要成人之美啊!』死缠着对方可不是我的本性与作为啊。或许,和熊爹的关系就随撕去的照片埋葬吧!」...想着,想着,阿翼伴随这些恼人未解的问题也遁入梦乡。...
晕倒的熊爹在张伯的陪同及救护车的紧急护送下,疾驶到最近的荣总医院。在急诊室里,熊爹躺了一晚,不仅熊爹夫人急忙的赶到医院看护,张太太也一同来到照料。近凌晨时,张伯夫妇才告别离去。
握着熊爹的手,夫人一刻也不能入眠,这突然而来的意外可是头一遭,却着实吓着了夫人。医生虽说无大碍,只要多休息一两天就好了,但多虑的夫人还是不安心,硬是撑着沉重疲累的眼睛陪在熊爹身侧。...
隔日上课,阿翼抑制着那些风花雪月,抑制着那些私领域恼人的事件与情绪,亦接连的上了三四节课。工作的重心就是上好每一节课,如果太受私领域情绪影响,不仅上不好课,连自己与学生的情绪都会受影响,这可不是阿翼自己愿意乐见。
每节下课,阿翼总会从抽屉里拿出手机,察看熊爹有没有拨电话过来,未接来电中,依然只有白伯寻觅与忏悔的电话及简讯。下班前的那一刻,仍没见着熊爹半通电话。离校返家的那一刻,浓重又强烈的失落感漫洒在阿翼荒芜的心田里,如漫生的杂草扩散开来。
心何以彷徨起来?何以担忧起来?该忘掉那无情的人才是啊?为什么自己仍然念念不忘?他不是该爱的人啊?为什么自己仍如此优柔寡断?本该灰飞湮灭的啊,为什么灰烬中自己仍望见火花?...
熊爹撑开眼睛,夫人手心的温暖传递了过来,夫人担忧的说着:「孩子的爹,你可不要吓我,孩子我可以不要,但是,我可不能没有你啊!」熊爹问了问夫人:「太太,我躺了多久,现在几点了。」夫人说着:「都晚上十点多了,你昏迷一天多了。」熊爹极力想着,该怎么排开夫人打电话给阿翼,近破灭的感情,可不能因为自己躺在病床上而坏了大事。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