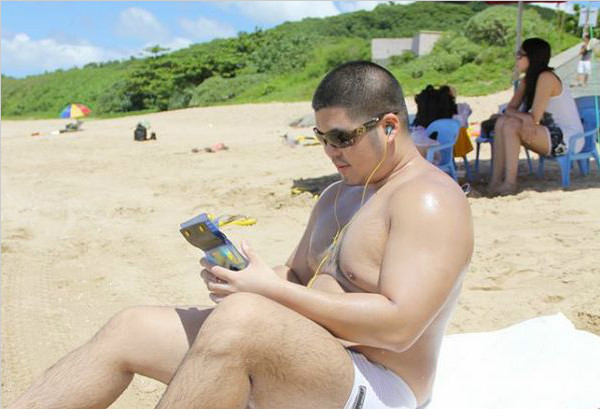中年男人和毕业生合租
以后要照顾好家庭,不过有在家里排遣不了的烦恼,老哥随时给你解决,毕竟人都需要有一个排解烦闷的渠道,理解我的意思吗?我问他。
你说的和不说的我都能理解,我说的和没说的你也知道。小云也说你是个好人。他笑了。
哎!你的胳膊怎么样了?明天请个假,我领你去医院看看。我忽然想起了正事儿。
他嘿嘿笑了。
我彻底晕了。小店的生意还算不错,按部就班营业就可以了,正如我目前的生活,心情平静而没有烦恼。
我理想中的幸福就是这样,有时候耐心地为客户介绍商品,语调平缓。有时候坐在店里,放一首音乐,平淡的目光投向窗外。身体没有不适,心中从容淡定。
有时候偶尔会想小冬现在在做什么,他是不是也在闲暇的时候想起我这个老哥。小冬曾经说过,每当喝着我给买的咖啡,当甜甜的味道回荡在口腔,仿佛感觉我就在他的身边。小冬不喜欢苦味的咖啡。他说过,生活就应该看似平淡,但平淡中偶尔会泛起淡淡的甜甜的味道。
每天我都用小飞剃须,其实以前我一直在用吉列刀片刮胡子,曾经买过几个电动的剃须刀,但是由于胡茬太硬,剃须刀总是损坏。有一次我在家休假三天,特意没刮胡子,结果满脸的络腮胡须一下子就让本来就不年轻的我老了十岁。刚开始用小飞的时候也不是很习惯,总觉得太过温柔,后来渐渐地才感觉到了舒服,每次使用时仿佛就是小冬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面颊。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又是冬季。东北的冬天很冷。有一天小冬来电话说他的母亲生病了,住进了市里的一家医院。我连忙把店交给伙计,在小冬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一丝不安。来到医院的时候,小冬和小云正在走廊里等我,小冬满脸憔悴,小云不安地在旁边站着。我问情况怎么样,小冬说早晨来的时候是父亲背下车的,当时母亲还能说话,现在母亲已经昏迷了。小冬的父母住在距离市里几百公里的乡下,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有些迷信,弟弟在上初中,一家都是本份人。距离他们村子四五里地有一个小山,山上有一座小庙,小冬的母亲总是抽空去庙里上香。前几天傍晚的时候母亲又去庙里了,可是天都黑了还没有回来。父亲很着急,和左邻右舍一起去找,半路上遇见了母亲。原来母亲在山上走迷糊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其实当时母亲的双脚已经冻坏了,但是害怕父亲责怪,就没知声。三天以后,当父亲发现时,母亲的双脚已经溃烂,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才住进了医院。由于刚冻坏的时候母亲自己偷偷用土方治疗,现在已经严重感染,陷入昏迷,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
病房里只开着一盏昏暗的灯,小冬的母亲上了呼吸机,小冬的父亲本来瘦小的身躯又佝偻了许多。因为医生说要预防传染,我没有让小云进屋。握住小冬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没有多说什么。
再次和小冬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是在殡仪馆里,她躺在棺材里,我和小冬披着棉大衣在守灵。不时地有小冬的亲属和同事、同学过来向老人鞠躬行礼,我和小冬沉默地站起来还礼。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面对面坐着,很少说话,不时地为老人烧一些纸钱。
忙着帮小冬张罗完丧事,我知道小冬需要平静几天,就没有打扰他。
过了一年,小冬结婚了。我参加了他的婚礼。
小冬的弟弟初中毕业了,不想继续念书,小云的父母在市里给找了家汽车修理厂,让他在那里打工,住在小冬家。我和小冬的弟弟吃过饭,小孩很老实,话很少。
过了一段时间,小东说最近弟弟很懒。以前的时候话虽然不多但很会来事儿,手脚勤快,经常帮着做一些家务。但是最近一回家就往床上一躺,什么都不愿意做,小云有些不高兴。我说过几天我找他吃饭,开导开导他。
再次接到小冬电话的时候,他问我是什么血型。原来小东的弟弟前段时间感觉乏力发烧,以为是感冒了,打了一周的点滴还不见好。后来医院一检查,结果是白血病。我的血型正好和小冬的弟弟相符,晕针的我在医院里闭着眼睛输血,我说我的身体比较好,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