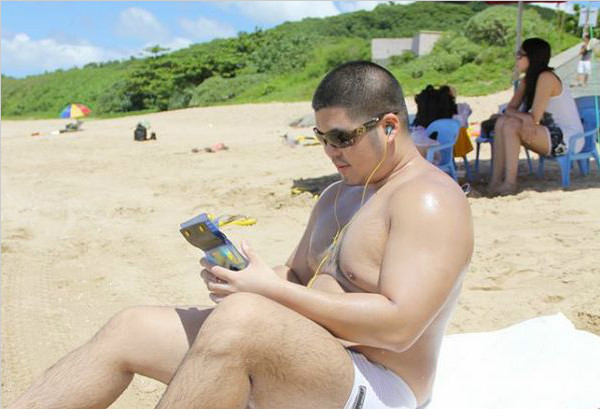我和表叔的故事
而事实是,我没去喝满月酒。老妈打电话来叫我去,我说要考试所以去不了,老妈也没对我多作刁难。
倒是满月酒之后的那个星期四,老妈和舅舅都来广州了,说是代表姑婆过来和表叔的亲家谈谈。
现在想来我真的不知道些关于他们婚后的生活,每次的电话基本都是说些日常工作生活的事情,我们的默契促使我们都避而不谈结婚生子新房子。
逐渐听着他从一开始还会沮丧到后来慢慢平静有时还高兴的语调变化,我知道我的目的快达到了。这场大戏骗过了他。
那个星期四晚上,老妈打电话过来叫我过去表叔新家吃饭,说是吃完再送我回来宿舍。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的时候,刚好在网上遇到瘦子哥,我问他,瘦子哥说,"去吧,不要等到以后没有办法回头了才后悔。"
那就试试吧,以后始终要在这种那种类似的场合里以亲人身份共处,如果第一步都踏不出那谈何以后。
决定了过去之后接到了表叔的电话。
"晏仔,我过去接你吧。"
"嗯。"听得到那边有舅舅和老妈的声音,我也不好多作推搪,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表叔的新家在哪里。
表叔的新家,措辞不能再用我们的家。
到了校门口之后等了一会表叔就到了。拉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动作有点生疏。端坐着说话时甚至不敢看表叔的脸。
对上一次见面还是某次他来学校找我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学校门口附近的一间过桥米线店里,各自吃着自己的超大碗的米线,各自在说着自己的生活工作。
这次坐上表叔的车,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自然。大概是太多的故事细节都发生在这吧,我们的家已经不在了,房子退了租客换了,剩下能见证我们过去的就只剩下这辆凌志了。
依然是我们一起买的小靠枕,依然是我喜欢闻的车内香水味。表叔拉开前座的小抽屉,拿出一张纸递了给我。我没打开也知道是什么纸。
那是去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深圳H driving, hot driver"四个单词,被我撕下放在了那小抽屉的最底层。
我拿着那张纸笑了笑,"还留着啊?"
"嗯,刚才想起来的。"还是在专心致志地开车,似乎又瘦了点,可是脸颊有了血气的痕迹。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颧骨,然后是下巴稍稍刺手的胡渣,继而是喉结和锁骨。表叔没有说话,还是在静静地开着车。
"有些东西,还是收拾干净比较好。"我笑了笑对他说着,继续进行着自己心里的计划。
可是我这个连小学时候的作业本都舍不得扔的人又怎么会舍得扔掉我们之间的回忆呢?
表叔大概忘了我这个怀旧的毛病,平静地"嗯"了一声。
去到表叔家的时候,我加入了餐桌。老妈把席间我的埋头吃饭寡言少语归纳成又突然犯害羞病,可是我想我和表叔都明白我在逃避着的是什么。我逃避的是坐在对面的这对主人和谐的画面,我逃避的是心中爱人的双眼,我逃避的是害怕自己演了那么久的戏一下子就被沮丧的眼神给败坏。
吃完饭之后老妈去了洗碗,表叔表婶和舅舅坐在客厅上聊着些照顾孩子该注意的东西,我坐在一旁玩着手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说不上什么。
小彦躺在房间里突然发出刺耳的哭声,大概是尿裤子饿了或者睡醒了。表婶走了进去房间,我才敢看表婶的身影,穿着好看的碎花长裙和简单的帽衫,大概是为了生孩子而剪断了的头发显得很清爽。
这个人和我的爱人多相配,我暗自想着。
等到他们想起我还要回宿舍的时候已经十点多快十一点了,宿舍十一点关门,已然是不可能回去宿舍。舅舅和老妈订了酒店,本来想说叫我一起过去再开间房,表叔说家里客房收拾下就行了不用麻烦,老妈想了想就要我留在表叔家睡。
我不想说表叔要我留下睡在客房的举动有多残忍,我只知道我那会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
脱了牛仔裤只穿着汗衫和内裤躺下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第二天还有早课,我想强迫自己快点入睡,无果。
房间的装饰很简洁,其实可以算是没有装饰。简单的天花,衣柜,书桌,床,便再无其他家具或装潢饰品。窗外是华灯遍布的羊城。
戴上耳塞开始随机播放绍军借我的mp3里的歌,一遍一遍地躲避着一些听了会令人更为精神亢奋的歌,直到听到王力宏的声音响满耳蜗。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