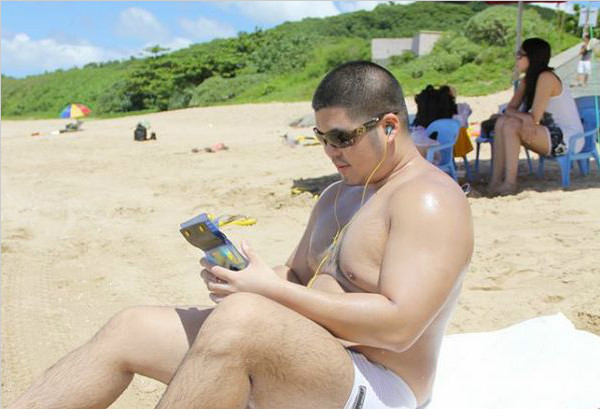我和表叔的故事
我乍听之下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是哪个表叔,妈妈可能看出我的疑问,继而说,"就是阿权表叔,小时候和你一起抢房间那个。"我听了之后也只是随口回答着几句话。接下来的话都记不得了,大抵是些妈妈的唠叨吧。
于是第二天我就拉着一个行李箱,潇洒地坐上爸爸的车,前往广州开展了新生活。大学刚开始那会,我刻意克制着自己,享受着等待某个自己爱的人过程中的孤独。也没打过电话给表叔,可能以为这样就可以忘记过去了吧。对于大一刚开学那段时间的记忆真的不是很清晰,唯有一笔带过。
国庆也没回家,广州的车站一到节假日就挤得像罐头一样,想想都觉得可怕于是就决定留在学校。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在这个假期会去拜访下表叔,那就错了。对于极其怕和别人挤,同时脸皮又极其薄的我来说,没有重要事我是不会去面对表叔的。国庆假期开始时宿舍六个人走剩两个,除我之外另外一个也在第三天去了投靠亲戚,临走还问我有没有亲戚在广州,我答说有,他便问我为什么不去投靠,我答说因为我曾经性骚扰她,他骂了句叼你就走了。我心想,我哪错了?说真话你还不信,嘿嘿。
自那次国庆假期,同在广州读书的叔伯兄弟约了我出去一次后,就因为我喝酒痛快所以经常约我。一起玩闹也不外乎用东莞话大聊特聊学校的事情,或者喝酒,或者唱歌。我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并且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为这种某程度上的理想而奋斗,爱情在那时的我的心中占得一二分,不足挂齿。
去拜访表叔,是我十一月底回家之后的事。我生日在十一月底,接了妈妈的一通电话就决定周末回家庆祝生日。回家之后无非也就是一堆亲戚坐在一起吃顿饭。末了,我回房间看书,妈妈拿着一小包东西跟了进来。
"有没有去找过表叔啊?"妈妈坐在我床边问我。
"没有,开学又要军训什么的,没时间啊。"我也只好实话实说,应该是老妈问了表叔才来跟我说的。
"表叔都打过好几次电话来了,说也没见你打他电话,他打你电话你又不接。"老妈看起来老了,比以前老了。
"哦。"我叼,你他妈的从来没打过一次电话过来还在你表姐我老妈那告我黑状?!
老妈把那包砂仁放在我桌面上就走了,说是外婆自己晒的要我拿去给表叔熬汤。(某种药材吧,表叔肠胃不好,这东西熬汤貌似有养胃的功效,我也不清楚)我拿起来看了看,打了几拳,我不就小时候不懂事摸了你几下,至于告我黑状嘛。
我还就不信你敢拿我怎样。于是回广州之后就趁着星期一下午没课,小心翼翼地斟酌措辞发了条短信问他地址就过去了。
那时表叔的家离我学校还挺远的,我坐了四站公车还要转三站地铁才到那个我用手机地图才找到的小区。敲了敲门,整理了下衣领和头发,表叔就开门了。
真的许久没见表叔了,时间久得我都差不多忘了表叔的样子。眼前的表叔穿着熨得笔直的西裤衬衣,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短发,和以前一样瘦。我恍了恍神,只对表叔笑了笑。
表叔把我迎进门拉我在沙发那坐下。普通的两房一厅,家具不多,客厅只有电视和沙发茶几,以及一盆看来不太翠绿的富贵竹。落地窗外有冬日的阳光。
"终于肯来探表叔啦?"表叔比以前成熟了,应该说老了,调侃的语气听起来是跑业务过程中养成的。
"没,入学忙啊。老妈叫我一定要拿这些砂仁给你,刚好星期一下午没课,所以我过来啦。"说着就把砂仁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他。
他笑了笑,接过去没说什么。太阳和地表间应该迎来了厚云层,窗外阴了些许。
后来坐了十几分钟大家都在说着些亲戚间常说的话,不外乎读大学比读中学轻松多了吧工作辛不辛苦之类的话题。看到电视机顶上放着张照片,是表叔和一个女人。
帅气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
我用玩笑的语气和表叔说,"表叔什么时候请喝喜酒啊?"
表叔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个相架,笑了笑,没直接回答,反而说"工作还没搞好,哪里敢提这个。"
临走时候表叔坚持要送我,可听到我说快四点半了,广州的交通高峰到了只好作罢。坐在电梯里,看着那一个个暗下来的按钮我却想起了许多东西。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