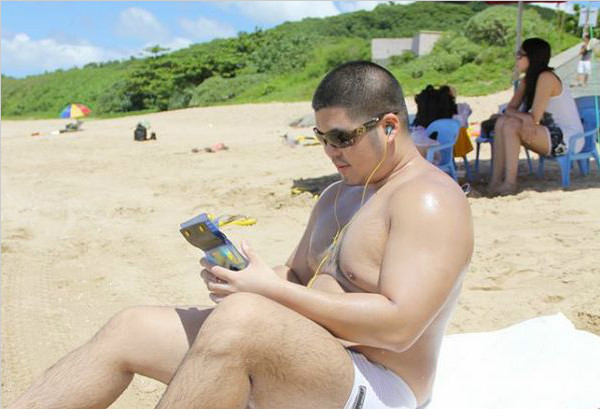早雾晴 晚雾阴
"与其受这样的折磨还不如早点死了好!哎呀!哎呀!"他的脚又开始疼了,情绪的激动会使他的脚剧烈的疼痛的,我俯下身用双手捧住他的脚不停地按摩。
"你不要这样激动了,这样会更疼的,你试着放松下来好吗?"没用,他依旧是疼得厉害,我只好下来找出止疼药给他服下,没忘了加了片安定药。
过了大概一小时他的腿有了点热气了,也安静下来了,睡着了。
………
我早早就起床了,由于药物的作用他睡的很沉稳,我把屋子打扫了一遍然后去买了点菜,准备他醒过来给他做点吃的。
罐哥也起来了,他在往门口摆他的酒箱子。
"君儒起这么早啊?"
"是啊,你也挺早的,我去买点菜,一会给老程做点饭。"
"他还没醒啊?他的脚怎么样了?"
"唉,昨天晚上又疼的厉害,折腾了一夜,我给他吃了药正睡呢。"
"干嘛不让他儿子回来啊,你和他非亲非故的,老这样也不好。"
"呵,话可不能这样说,咱们不都是朋友吗?朋友有了难处理应帮忙啊。"我很不愿意听他这样的话。
"也到是,脚疼有那么厉害吗?我到认为他是故意做样子的。"
"你到是也做做样子我看看,哼!"我懒得理他,扭头直接去菜市场了。
买菜回来,老程还在打着呼噜,为了不打扰他我搬出小凳子坐到门口摘菜。刚才冲了罐哥一句,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拿着烟过来了。
"抽支烟吧,刚才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接过来点上。
"我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疼真的不是装出来的,我看得出来。所以你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说,他要是听见会很伤心的。"
"哦,我记住了,昨天你不是和老皮蛋去安阳了吗 ?那边怎么说?"
"也没查出病因,唉!这到底是个什么病呢?"
"君儒,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只管对我说,多的我没有拿个几千的我还可以帮忙。"
"不用了,我还有钱,老程的病如果治疗有困难的话我再向你张口。"
"那也好。对了,市场到过了年要拆了,你还不知道吧。"
"早就听说了,谁知道是不是唬人呢。"
"这次应该是真的,我们每个门市都给了张通知,要求在年前必须全部搬走,这里要重盖了。"
"哦,那得跟老程说说这事,让他趁早租房子。"
"你看,清清来了。"他朝着大门口的方向指了指,"应该是朝这来的。"
我抬头一看,清清和一个男的一起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我拿着菜就想进屋,没想到她喊了我一声。
"君儒,我有事找你。"说话他们俩就到了我跟前,罐哥起身走了。她和那人下来车子走到我跟前说:"君儒,程伯伯的病怎么样了?"
"昨天去安阳检查了,也没检查出什么结果,我再搬几个凳子,你们坐吧。"
"哦,忘了告诉你,这位是我的对象,我们到腊月十六结婚,你和程伯伯一定要来啊。"他对象看起来的确和我有相似之处,我笑着和他握了下手。
"好的,我们一定去。"
"对了君儒,我主要是来想告诉你,程伯伯的病可以去北京治,他爷爷原来就是因为指头疼后来截肢了,但是截肢后手也疼起来,又把手给截了,截了手之后小臂又疼起来,后来又要截小臂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了北京的医院,到那做了个手术就好了,现在也不疼了。"他对象在跟前点着头。
"是这样的,清清一跟我说,我就想起我爷爷的病了,截肢是不能祛除病根的,你最好和程伯伯去北京看看,肯定能治好。"他一脸的肯定。
"是吗?我一定告诉他。"有了这样的病例我想老程一定会增加信心的,我迫切地想让他知道,但他还在睡,我只好忍着兴奋和他俩继续聊着。
我把清清男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告诉了他,他没表现出有多大的兴奋,只是不再拒绝去北京的事了。我让他请示一了下局里,但那边好象对他这个病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他卧床快一月了吧,也没见一个人来看望过他,只是厂里的那个副经理来过一次,但只是坐了十分钟就走了,这样人走茶凉的情景使我感觉到了一种悲凉。
走在五街的街道上,邻居带着嘲弄似的口吻问我老程的病怎样,我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好象他是故意装出来的。但同时我也理解邻居们,在他们看来脚疼算不上什么大病,最多把脚截肢了按个假的罢了,但终究那不是一码事,清清的男朋友那一席话我才认识到不是截肢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找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