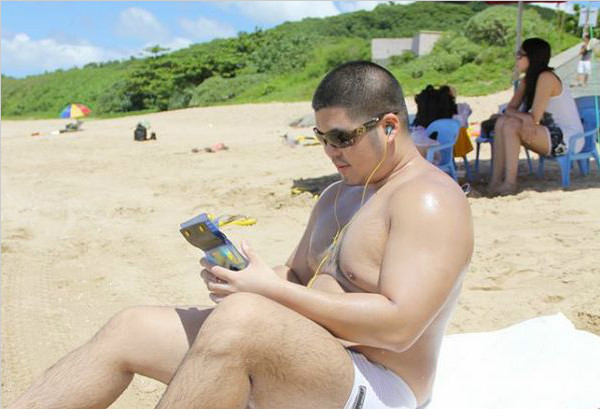转角遇见熊爹
张伯与熊爹躺坐在汤池里面,双脚交叉靠着,熊爹闭起眼睛,什么话也不想说,被张伯霸王硬上弓的强迫了来,现在还得进个人池挑战自己情欲的尺度,他不清楚,等下张伯的热情他该如何拒绝才是。还记得中国谚语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那根本是骗人的嘛!今儿的船似乎直不了,可能如铁达尼号一样,会撞冰山的。
想着想着的同时,池内热水显明的波动着,一股热流也随之而来,暖着皮肤,也燃起了自我防卫的机制。熊爹正想睁眼瞧个究竟时,张伯的嘴早就嘟往熊爹的唇,双手更是紧紧的盖着熊爹的双耳。熊爹双手用力想撑开张伯的手,头更是左右的摆动闪躲,但越是闪躲与出力,张伯的唇贴的更紧,连舌头更是想突破熊爹紧闭的唇。
随着身体的下滑,熊爹的挣扎也快没了力,如泄了气的皮球,熊爹放弃般的放开了用力扳开张伯的手,连嘴也失守的微微张起,两人的舌头也瞬间的纠缠在一起。张伯一手撑着熊爹的后脑杓,一手抚着熊爹性格的胸毛及腹毛,方才的强硬也化为柔情的爱抚。
「为何自己这么的无能?为何自己守不住最后的防线?这些都可以避免的啊,为何还是被牵着鼻子走?给弟弟的承诺难道这么经不起考验吗?」一阵一阵的自我对话在吻着的同时,也不断的在脑海中翻飞着。
熊爹的脸混着汗珠混着泪,混乱的情欲关系进行着,失守的情欲界线如地牛翻身摇晃着方寸,撕裂着心。...
阿翼醒来时,身体光溜溜的躺在软床上,白伯的一手一脚更也夹抱着阿翼,一丝不挂的侧卧在阿翼身旁。床头灯微微散着黄晕,阿翼望见白伯甜美的笑容洒在嘴角上。看了手上的表,指针指着三点15分。
摸着头,阿翼发现头仍隐隐微痛着,或许酒精还没完全散去吧!明明自己酒量还不错啊,为何会迷迷糊糊的醉了?酒醉里面,怎完全不清楚怎么被扒光衣服,怎么躺到这软床的。摸了摸下腹,阿翼感觉下腹有一股泄完精的空洞,明明好几天没有射精出来了啊,莫非....。混乱的思绪在脑中打转着,为何自己这么不小心?怎把关系弄成这样?
阿翼轻手轻脚的挪开了白伯的身体,白伯鼾声依然持续响着。翻了翻垃圾桶,一沱一沱的卫生纸躺在里面,阿翼小心的摊了开,里头包裹着用完的一只保险套。...「为什么自己一点知觉都没有,真该死。」阿翼用力地在自己脑上重垂了两下,很无力,很无奈,但事情发生了又能怎样?
阿翼很快的穿回衣裤,临走前留下了张字条:「感谢这几个礼拜的相知相遇,我有爱人了,所以一直跨不出与您的互动。我知道你是好人,但现阶段的我是无法接纳和你的关系的。我不应该答应让这段关系进行的,也不值得你对我的好。如今关系变了,我们又该维持怎样的关系呢?我不清楚,真的迷糊了。儿阿翼3:30。PS:这阵子我不会再去健身房了,也不会接你电话了,让我先冷静冷静处理我的感情吧。」....
学校里,阿翼递出了县外介聘的申请资料,地点不是老家高雄,而是熊爹居住的台北市。同事们纷纷关心的问着:「阿翼,你老家不是在高雄吗?干嘛调去台北市,台北市很难进去的ㄟ。」「范老师,女朋友在台北市喔,赶快结婚啦,加九十分还是一百二十分的喔!」对于久待此校的阿翼,同事在碰头时总会关心的问着。
大学死党阿文也拨电话来询问:「阿翼,你不是要和我们学校的主任互调吗?现在还要吗?我主任还问着。要调回来要快点,以后县外缺会越来越少喔。」同校服务的大学室友阿龙也好奇的说着:「喂,你搞什么,我们几个学长学弟都在这里好好的,干嘛还调去台北市?调回去高雄还说的通,干嘛无聊跑去台北市?你怪怪的喔!」
阿翼都只是轻轻的回着:「没什么,只想成为台北市人,原因就这么单纯。」不熟的同事只是笑笑的回着,没多说什么。熟稔的同事都念着:「当台北县县民有什么不好?有差吗?」
这些问答或是关心,或是客套,每当调动时,这些对话总会适时的出现,很是烦人,但简单应付还是没啥问题的。其实,深层最主要的原因没人知道,除了阿翼以前同事兼干妹妹知道外,其余人知道的不过是表象挤出来的客套话。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