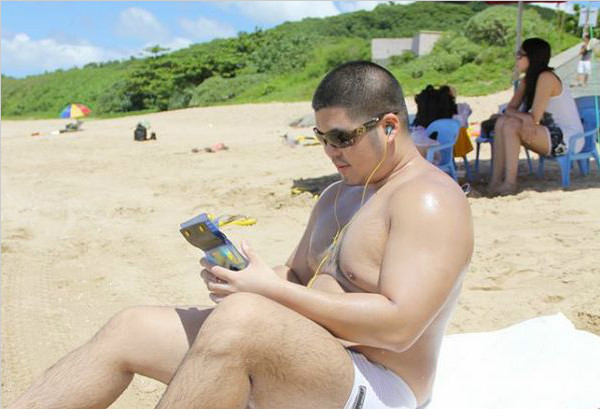中年男人和毕业生合租
我说这很好啊,谁在单位里没几个知己啊!
他说,老哥你好像什么时候都不吃醋。
我说我吃得着嘛!南方,冬小麦的主要产区正在抗旱,而我所在的县城,这个冬天的雪厚于往年,街道两旁的雪堆了老高,街面上的积雪刚刚被刮雪机清理干净,这不,从今天清晨开始,这雪就没有停的意思,有些纷纷扬扬的味道。早晨上班等车的时候,飞扬的雪花避过遮挡我头部的帽子,挂在了睫毛上。下车的时候,脚下一滑,右腿屈膝支地,差点没把我的玻璃盖儿卡秃喽皮了,还好,右手摁在了雪上,不至于受伤。雪花在我的掌心渐渐化开,这是一片干净的濡湿。
其实,无论雪下了多少,细算起来,自己和雪的亲密接触在一天当中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是在屋里看着窗外,看着行人在雪地上行走,雪在他们的脚下一定发出了吱呀的响声。可能,没有人行走的雪地是寂寞的,可是遍布深浅足痕的雪地总是满目伤痕。见惯了雪的人们,除了匆匆赶路,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景致。
中午下班,打电话给小冬,我说忽然很想去吃砂锅,这么一个大雪天,吃点砂锅,心里暖和。他说有事来不了。
这是一家老店。服侍客人们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她忙前忙后的。我点了一大碗米饭,一个砂锅土豆丝,一碗坛肉。等了一会,一个服务生从后台端出一个热气腾腾的砂锅,中年女士赶紧毛拉争光地说,这是六号桌那位老爷子的。见服务生向我走来,我一愣。呵呵,十年前我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第一次听见卖菜的小姑娘喊我一声大叔,当时我愣了半天才从大哥转为大叔的称呼中醒过神来。此时我一打量自己的打扮:脸色本来就不白,胡子也两天没刮了,下巴上一定又长出了几根白胡须,棉服的颜色灰暗,表情沉闷,我不禁莞尔。服务生朝中年女士一乐,已觉失言的女士有些不好意思。还好,米饭松软,土豆丝清淡,坛肉中的瘦肉烂而不柴,肥肉软而不腻。我把土豆丝和热汤还有坛肉和米饭搅拌在一起,放点辣椒油,拿起小勺,想象韩剧中吃拌饭的样子,一勺接一勺,啊!好爽口。
小店又进来了客人,我一回头,看见小冬和一个人说笑着进来了,一边跺着脚上的雪一边说今年这雪真大。
看见了我,小冬没有惊讶,反正我在他的表情中没有捕捉到一丝的意外。打个淡淡的招呼之后就路过了。
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男士,看样子可能比我小一些,毫不谦虚地说,和他相比我在外表上很逊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和他相比较的想法。甚至我想,如果我的拌饭里现在加一点点醋,滋味会变得如何。
二位的座位距离我不远,我甚至可以听见俩人交谈正欢的声音,小冬的笑声似乎有些做作,在公共场合,这样的笑声有些醒目,我微微皱眉。我听见他大声地说,给我来一个砂锅土豆丝,一碗肉。
只要我抬头,完全就可以看见小冬,他和我对面,但我一直在闷头默默吃饭,细嚼慢咽的样子,表情不露声色。但是在口感上,感觉这拌饭渐渐在嘴里就没了滋味。我想,如果多放些辣椒油,也许才能吃出滋味。
服务员,来点辣椒油!我喊道,小声地喊着,保持着自己的风度。
老哥,服务员太忙,您就别折腾了。这是我那桌的,您老现用着!加点醋更好吃,不够我给你要。服务员没来,小冬给我送来了一罐辣椒油和一罐醋,一个粗糙的华丽转身后就又回去谈笑风生了。
我忍住了想喝酒的欲望,只添加了一点点辣椒油,依旧闷头,依旧文雅。食毕,买单的时候,我狠了狠心,悄悄地对收款的中年女士说,大姐,一看就知道您顶多大我几岁,但是您看着挺年轻,看上去也就和我一般大。女士似乎要哭,尴尬得有些不知所措。为了弥补自己的口无遮拦,我在心里暗暗祝愿她今天的收款能够分毫不差。起身,微笑着和小冬点头告别。他的男人也回头和我点点头。
晚上下班的时候,雪儿终于停了。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李先生牛肉面了。
一大碗鸡丝面,一盘秘制牛肉,一碟儿麻辣黄瓜,要了一瓶啤酒,想了想又要了一瓶。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