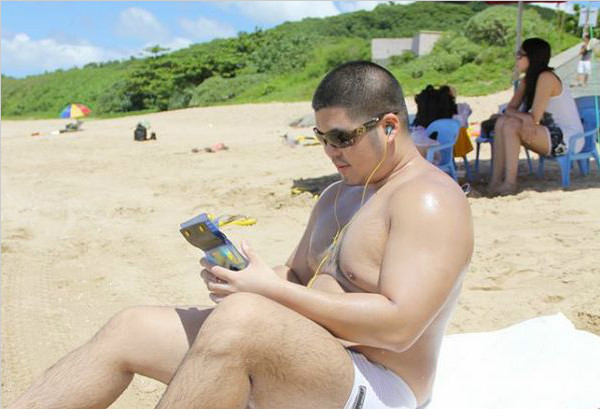我的语文老师
我点点头。然后我对大哥说:
"哥,我不走了,改天再走,我退车票去。"
"阿勇,你回学校去吧,别退车票了,要扣手续费的。哥已经见到你了,知道你很好就可以了,你赶快去上车吧。听话啊,勇。"
我很执著地摇着头,不,我一定要留下来,我有太多的话要对我大哥说。
我把东西放在大哥的水果摊底下,马上跑去了售票厅。很快,我就回来了,我坐在水果摊后面,坐在大哥身边,大哥再没说什么,我也没有说话,我就那么坐在那里静静地陪着我大哥。陪着大哥做生意,看着大哥平平安安,那也是一种幸福。
下午我们早早收摊了,我帮着大哥收拾那些东西。旁边同做生意一个老者不解地问他,怎么回去这么早.他对老者说:"金爹,我弟弟来了,明天他还要赶北京读书去呢。"
没有推车,大哥把那些水果装进箱里,然后打捆挑回去。大哥挑着担走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就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样把那担子担得那么娴熟,我不禁想起刚来我家挑谷子的时候,寨里的人都笑他三兄弟并排走,那担子横着挑得晃晃悠悠的,几年的功夫,我那个贫困的家让他变得比一个农民还要农民了。、
大哥挑着担子把我领到一栋大楼的地下室,那地下室挺矮挺暗,被隔成了小小的像鸽子笼一样的小间的阁室,这些小阁室是城里人用来堆放杂物的。我们在一间阁室前停了下来.
大哥把门打开后,叫我先别进去,他进去把一个燃着的煤炉提了出来,放在门外,然后把门大开,让里面满室的煤气跑出来。等了好久,我们才进去,但是室内的煤气味还是很浓。房间是无法想像的窄小,放了一张床后,连一张桌子都摆不下了。那张单人床上只有一床被子,床上就连枕头也都没有。也就是说,那间小房子里(如果也称得上房的话)除了一张床,一个煤炉,一口小锅,几个碗,一把菜刀,什么也没有了。整个房子没有一本书,或是一口小箱子,那怕是我们念初中时那种家里自制的木箱也没有。你无法想象,现在在这间房子里居住的人原来是一名大学生,是一名老师。
大哥在门外把担子解开,然后把那些水果一箱箱搬进来放在床下面,他不让我动手,而且,两个人搬的话也无法转身。
晚饭我们没有自己做,兄弟俩在外面吃的快餐。吃完饭后,大哥把我带到一家旅舍,当站在服务台前时,我拼命地把大哥扯了过来,我直直地看着他,他避开了我的眼睛。我问他:
"哥,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给你挂个铺,你看,我那儿像个狗窝,再说,你也要好好睡一晚上,还要坐那么久的火车呢。"
"我就要跟你睡,哥,你每天晚上都睡在那里,勇勇睡一个晚上就不可以了?"
说完我走了出来,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
大哥无可奈何地跟了出来。
那是一座似曾相识的陌生的城市。我挽着大哥的手臂,就像挽着自己爱人的手臂一样,在这里我不畏人言。我知道大哥也喜欢我这样挽着他也渴望我这样挽着他。我们慢慢地走在那些大街小巷上,那些街那些巷,我们曾经走过,在这里曾经留下过我们幸福的欢声笑语。今天我们又走在这里,默默无言,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回想我初三毕业考试结束后的那个夜晚。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停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生一世。
晚上我和大哥一起回到了他的房间,他把他的衣服脱下给我做了枕头。当我准备在大哥面前一件件把自己的衣服脱掉的时候,大哥把我制止了,他说你就穿着衣服睡吧,要不晚上太冷。我没听他的,我在他前面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包括我的内裤,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把我的裸体展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听见大哥重重地叹了口气。
"睡吧,别着凉了,勇。"
他静静地坐在床沿上,没有任何动静。
我没有上床。我赤裸着走到大哥面前,我拿起大哥的手,把他的双手放在我的腰上,我要他抱着我。
他没有,我的手放开后,他的手又垂了下来。
我好伤心,我把大哥的头捧起,注视着他,问他:
"怎么了,哥,不要勇勇了?"
他摇了摇头。
不管他同不同意,我便开始解他的衣扣,他没有反抗,他的棉衣一进门就脱了给我做了枕头,身上其余的衣服是我一件件亲手脱掉的.我们俩都赤裸裸的了,我把脸贴在大哥的胸膛上,轻轻地对大哥说: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