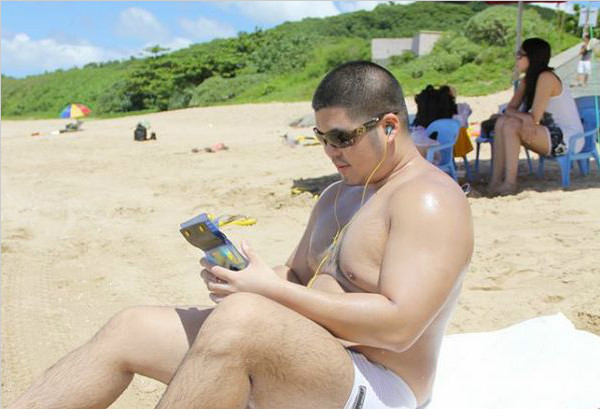兄弟,听到请回答
在黑夜里独自与一个死人相伴,总觉得那个死人会活过来。杜大华也觉得程贤进应该会活过来,他甚至听见程贤进在说话,其实他听到的只是崖畔上的夜鸟在叫。也不一定是夜鸟,崖畔上的东西多得很,既有飞禽,也有走兽,还有多年前挂上去的悬棺。在山脚下看不见悬棺,要在河的对面才能看见,有人说,更深人静时从这个弯道经过,能听到悬棺呵呵笑。
"我的好兄弟呀,"杜大华用自己的手抚着程贤进的脸,"你不就是要一千块钱吗?一千块钱算个啥卵事啊,我给你不就得了吗?我当时荷包里没有,回家去拿来再给你不行吗?我给了你,还不会去找开采队报账,就算我自己给的——我为啥要敲死你呀!"
说了这句话,杜大华的皮肤底下嘶嘶嘶地蹿动着寒气。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程贤进喊下山来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了准备,不然为什么要提个菠萝槌呢?菠萝槌是他从一棵老松上砍下的,刚刚砍断,程贤进叫他的声音就一波一波地逼上来了。那声音被空气擦得发热,发出哔哔剥剥的亮光。这不是善意的声音。自从他俩喝了那台不该喝的酒,程贤进就没对他发出过善意的声音。他应了一声。可声音是朝上跑的,程贤进喊他,他能听见,他应这一声程贤进不一定能听见,于是他拔腿就往山下跑,都跑下一道塄坎了,又反身回去,提上了砍柴刀。想想不对,人家叫你,又没说要跟你打架,你把砍柴刀提上干啥?村里人砍柴,只要活没做完,刀都是留在那里的,又没人偷。他把刀丢下,可他觉得,这么空手下山,到底不行,这才又提上了那个菠萝槌。菠萝槌个头并不大,但沉甸甸的,至少有二十斤重。到了程贤进跟前,两人刚对了几句话,杜大华就转到程贤进身后,站到了那个土堆上。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如果杜大华没有准备,他会这么做吗?
这是一个深渊,欲望的深渊在操作自己,和他分开了,还想让他消失。杜大华不敢俯视。
"我没有歹意呀,"他为自己辩护,"即使有,哪会在人前给你一槌?我是情急之中才挥过去的,在那之前,我根本没打算把手里的家伙派上用场。"
&nb sp;他痛骂起来。他骂的是那个菠萝槌。他说你个狗日的,你再没地方长,也不该长到那片柴山里,长到那片柴山里,也不该让我碰见;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长在那里是犯罪啊,你把我的好兄弟给敲死了啊……把他敲死了,我杜大华也就活不下去了……
他抬眼朝镇上望去。回龙镇这名字听上去很霸气,以前却是这条河上最冷清的,自从老君山发现了矿藏,来了开采队和外国专家,才迅速地灯红酒绿起来。尽管镇子那边悄无声息,但杜大华知道,那里的人都在滋滋润润地活着,他们喝酒、打牌、抽烟、调情、做爱……杜大华一直都在那么过着,特别是他跟李队长去大荒洞谈话之后日日夜夜都浸泡其中,以前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与程贤进喝了那次酒过后,他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的"不适应",就像从黑暗处猛然进入一间被灯光照得雪亮的屋子,眼睛不得不眯缝一下,当这一阵过去,他发现,没有什么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理所当然",杜大华几乎淡忘了那种生活的滋味。而此时此刻,所有的滋味都裹挟在河风里,扑面而来,所有的滋味都那么新鲜和珍贵!
在镇上,还有他的儿子呢。他猜想,儿子肯定没参与闹新房,而是站在主人家的音响前,举着麦克风自顾自地唱歌。先前他喜欢晶晶,晶晶也喜欢他,这事他们没给父母谈过,但瞒不过父母的眼睛。杜大华和程贤进之间虽然从未把话说透,但彼此心照不宣,都只是等着时候一到,两人就由兄弟变为亲家。谁知道会出那样的事!要是不出那事,杜大华相信他就不会跟程贤进喝那次酒,即便喝酒,也不会喝出那样的后果。现在,比晶晶大两岁的儿子还没订亲呢,而且一给他谈起这事他就发火,就躲在县城几天几夜不回来,连生意也懒得做。
仔细想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杜大华放得下的。
儿子、妻子、采沙船和快艇,还有他的村长以及围绕其间的所有关系,都放不下。
使劲一拳击打在程贤进的头上。
程贤进的头像皮球那样弹了几弹,又复归平静。
-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
{{item.user.user_nickname}} {{item.create_time_str}}{{item.content}}{{item.like_count}} {{item.reply_count}}